导读:随着立法层面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迫切需要对该制度构成要件的认定加以探讨。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侵权人故意”“严重侵权后果”以及“权利人提出申请”为构成要件,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
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常见情形是,没有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的意见。在寻求和遵循适格律师意见过程中,故意侵权认定的标准出现了从宽松到严格再到相对宽松的演变历程,意图实现权利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最终落脚到被控侵权人的动机或者意愿上。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构成要件最关键的抗辩理由是被控侵权人具有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从程序法角度而言,证明构成故意应当遵循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来源:《知识产权》2017年第5期
2013年修正后的《商标法》已经明确引入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2014年6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1]中均探索从立法层面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说,我国即将全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随着立法层面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迫切需要对该制度的构成要件认定加以探讨,以期对未来法律实践有所指引。
就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而言,主要包括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认定两个方面。结合制度价值和制度定位,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以“侵权人故意”、“严重侵权后果”以及“权利人提出申请”为构成要件[2]。亦即,从客观方面而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存在严重侵权后果的情况,这一点主要通过证据对侵权后果进行证明。从主观方面而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故意侵权[3],乃至恶意侵权或者明显不当行为的情况下[4],正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案[5]中所表述的,只有当侵权是故意侵权的时候,才能提高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当被控侵权人是善意的,甚至实质上挑战专利权的有效性或者就专利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进行抗辩的时候,判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不适当的。因此,在法律构成要件认定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
一、故意的认定:是否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意见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故意侵权”作为适用条件,“因为经常用于惩罚侵权者的故意,这一提高的损害赔偿金由此具有惩罚性质”[6],这也是由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所决定的[7]。然而,故意是一种心理状态,需要通过当事人的行为加以判断。如果被控侵权人没有意识到知识产权的存在,就不能认定构成故意侵权,这是认定故意侵权的最低门槛;如果被控侵权人意识到了知识产权的存在,他就具有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的法律责任,这就是认定故意侵权的较高标准[8]。
通常来说,根据认定故意侵权的较高标准,民事主体在收到权利人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函或者警告函的时候,具有尊重权利人知识产权的责任,这一尊重通常表现为寻求和遵循律师意见。因此,就法律实践来看,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常见情形是,是否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的意见。也就是说,没有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的意见,是构成故意侵权的关键因素。
首先,民事主体在收到权利人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函或者警告函的时候,具有寻求和遵循律师意见的义务。在水下装备公司诉莫里森·努森一案[9]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民事主体在收到专利权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的时候,具有积极注意义务以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可以寻求律师意见并遵照执行,对专利权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及时应对可以使得被控告侵权人不构成故意侵权,从而不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0]。
在该案中,被控侵权人的内部法律顾问经过查询提供了被控侵权人无需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意见,被控侵权人的内部法律顾问认为,涉案专利很可能被宣告无效并且强调“近些年相关声称被侵权的专利有近80%被宣告无效”。被控侵权人据此拒绝支付专利许可费。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声称其具有对律师意见的良好信任,不构成侵权故意。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认为,在收到专利权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之后,该被控侵权人具有积极义务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一积极义务包括,在任何可能的侵权行为开始之前,从律师处寻求和获得适格的法律咨询意见的义务。在该案中,被控侵权人的内部法律顾问进行了现有技术检索,但是并没有获得或者分析专利侵权行为发生之前该专利的审查历史,其法律意见在专利权的有效性和侵权判定方面仅有没有支持的结论性表述。
同时,被控侵权人明知这一法律意见来自其内部法律顾问并且其内部法律顾问没有专利代理资格,因此,该内部法律意见并非适格的法律意见,被控侵权人构成故意侵权。
其次,民事主体在收到权利人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律师函或者警告函的时候,具有寻求和遵循适格律师意见的义务。在中央豆制品公司诉荷美尔公司一案[11]中,与水下装备公司诉莫里森·努森一案有所不同的是,被控侵权人在实施专利侵权行为之前,获得了外部专利代理人关于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法律意见,并且该法律意见考察了专利申请审批的历史。
但是,美国巡回上诉法院仍然认为该法律意见并不适格。主要理由是,该法律意见关于专利权有效性的分析仅仅参考了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审查员和专利复审委员会给出的参考文献,被控侵权人用了两年时间未能充分确定其是否保持在法律意见所建议的参数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被控侵权人具有积极义务获得适格的法律意见以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一法律意见不仅需要达到适格的标准,还需要与其分析相匹配,做到法律结论得到分析的充分支撑。
因此,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意见的情况,是判断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存在着尽管没有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意见但是不构成故意侵权的个别情况,以及尽管寻求和遵循了称职律师意见但是仍然构成故意侵权的个别情况。
首先,就尽管没有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意见但是不构成故意侵权的个别情况而言,虽然没有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的意见是构成故意侵权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只是构成故意侵权的因素之一。例如,在美国原创公司诉詹金斯食品公司一案[12]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不认为构成故意侵权,该院指出,故意侵权需要结合整体情况综合判断,被控侵权人在专利授权后没有去寻求关于是否构成侵权的律师意见,但是被控侵权人改变了其生产系统以便于避免侵权,专利权人在提起诉讼之前并未向被控侵权人提出过侵权指控。
再如,在国王装备公司诉小谷公司(KingInstrument Corp. v. Otari Corp.)一案[13]中,虽然被控侵权人没有寻求律师意见,但是其检查了专利权人的早期产品并且提交了专利权人的改进专利申请,积极参加专利许可谈判,这些都表现出被控侵权人具有避免专利诉讼的意愿,因此不构成故意侵权。
其次,尽管寻求和遵循了称职律师意见但是仍然构成故意侵权的个别情况。如果被控侵权人寻求并获得了适格的律师意见,指出专利权无效或者不构成侵权,那么法院通常会认定不具有主观故意;在被控侵权人不完全称职,并未完全遵循律师意见等情形下,应当认定为其具有主观故意。但是,在蓄意抄袭、隐匿侵权行为等情况下,即使寻求和遵循了称职律师意见,仍然应当认定为其具有主观故意。
二、故意的标准:从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的并用向完全主观标准转变
在寻求和遵循适格律师意见过程中,故意侵权认定的标准出现了从宽松到严格再到相对宽松的演变历程,意图实现权利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宽松的认定标准:司法推定规则。美国早期的司法实践采取推定规则,对“故意”的认定较为宽松。亦即,如果被控侵权人不能提供律师意见,那么就推定被控侵权人构成“故意”,满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
例如,在克洛斯特超切钢诉熔炉公司一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被控侵权人无法提供律师意见,要么是因为被控侵权人没有从律师处得到法律意见,要么是因为被控侵权人从律师处得到了构成侵权的法律意见,因此可以做出对被控侵权人不利的推断,认定其构成“故意”。再如,在前述水下装备公司诉莫里森·努森一案[14]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民事主体在收到权利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的时候,具有积极注意义务以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可以寻求律师意见并遵照执行,对权利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及时应对可以使得被控告侵权人不构成故意侵权,从而不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5]。在该案中,对“故意”的认定类似于过失的标准,亦即缺乏一个理性的民事主体所应有的注意。
相对严格的认定标准:“瑞德标准”。在此之后的法律实践中,对“故意”认定标准逐步从宽松走向严格。在瑞德公司诉波泰克公司一案[16]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确立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故意”认定的“瑞德标准”,对法律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仅仅发现存在侵权故意不会导致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提高到三倍,确定数额的关键因素是根据所有因素和环境判断得出的被告行为的恶劣程度,法院在确定数额时应当考虑使得被控侵权人更加具有道德上可非难性的因素,以及会减轻或者降低被控侵权人道德上可非难性的因素。
因此,瑞德案给出了帮助法院确定被控侵权人主观恶意程度,从而确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以及惩罚性赔偿的具体倍数的9个考虑因素,这9个考虑因素在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方面的作用被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案[17]替代,但是其被成为认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倍数的主要标准。
这9个考虑因素包括:是被控侵权人蓄意抄袭了权利人的构思还是被控侵权人做出了另行的设计;当被控侵权人知晓了其他人拥有知识产权的时候,是否调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或者具有善意地认定该知识产权无效或者并非侵权的情况;被控侵权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行为;被告的企业规模和财务情况;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逼近客观事实的程度;被控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被控侵权人采取的补救行为;被控侵权人的侵权动机;被控侵权人企图隐藏其不正当行为的意图。
在此之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克诺尔集团诉丹拿公司一案[18]中进一步收紧“故意”的认定标准。在该案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由于律师存在对客户保密的义务有可能无法提供律师意见,不能单纯因为被控侵权人无法提供律师意见就推定其构成“故意”,同时这一推定也不是财产权领域的普遍规则,因此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也不应当提出特殊的要求。
全面严格的标准: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并用的“希捷标准”。全面严格化“故意”认定标准主要体现在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案[19]中,该案确立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故意”认定的“希捷标准”,对法律实践具有重要影响。该案中,被控侵权人的律师给出了专利权无效、不能执行等律师意见。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取全席判决的方式否定了上述判决有关积极注意义务的观点,认为被控侵权人没有获得律师的积极义务,应当采取轻率的注意义务标准判断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案在该案中明确了“故意侵权”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
一方面,为了证明故意侵权,专利权人必须以清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对侵犯有效的专利权的较高可能性有所认识,不顾客观上具有较高可能性构成侵权的情况,仍然轻率地、鲁莽地进行了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等行为,这是证明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的客观标准。其中所述的“鲁莽地”,通常是指民事主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一个理性的民事主体应当认识到,其行为是不合理的冒险行为,却仍然坚持进行这一行为[20]。这一判断的核心是,理性的民事主体是否具有较高可能性的认识,认识到其行为构成侵权。在专利侵权诉讼之前,被控侵权人是否获得适格的律师意见,可以用于证明是否存在此种“客观上较高可能性”的具体情形。在这一判断中,可以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人的侵权技术的类似度、在采取争议的侵权行为之前被控侵权人获得的律师意见、涉案专利所述领域的技术饱和度和创新空间、庭审中提出的抗辩事由情况。[21]
另一方面,为了证明故意侵权,专利权人还需要进一步证明,上述客观上定义的构成专利侵权的风险,被控侵权人已经知道以致于构成“明知”,或者侵权可能性非常明显以致于构成“应知”,这是证明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的主观标准。在这一判断中,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专利权人提供了明确的通知说明被控侵权人的特定行为会侵犯其专利权、被控侵权人在实施侵权行为之前获得的律师意见、专利权人与被控侵权人之间的关系、被控侵权人与本领域技术人员相比的能力差别、被控侵权产品上的标识、专利授权与商用化之间的时间间隔等[22]。
相对宽松的标准:对“希捷标准”的反思与向完全主观标准的转变。当前,美国司法实践出现了对较为严格的“希捷标准”的反思。2016年6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光环电子公司诉脉冲电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23]和斯特赖克公司等诉齐默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24]作出判决,调整了“希捷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美国专利法》第284条没有给出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精确规则,但是在美国专利制度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来的一百八十多年的法律实践中,该制度并不适用于一般的专利侵权行为,其主要用于“异乎寻常的、极其恶劣的专利侵权行为”,至于哪些行为属于适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异乎寻常的、极其恶劣的专利侵权行为”,这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一案所确立的“希捷标准”中的客观标准不符合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上述本意,仅应当保留“希捷标准”中的主观标准。
亦即,在证明“故意侵权”的过程中,不应当要求专利权人证明“被控侵权人对侵犯有效的专利权的较高可能性有所认识并鲁莽地进行了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等行为”,只需要证明被控侵权人对专利侵权的风险已经知道以致于构成“明知”或者侵权可能性非常明显以致于构成“应知”。“希捷标准”要求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证明被控侵权人存在客观上的鲁莽行为,这把许多蓄意的和肆意的专利侵权人都排除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该标准使得被控侵权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很容易就能编造一个借口进行抗辩,这种抗辩很有可能使被控侵权人避免惩罚性赔偿,甚至有些被控侵权人对专利的有效性毫不怀疑并且没有任何抗辩的借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侵犯他人的专利权、窃取他人的专利技术。
因此,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格性仅仅体现在被控侵权人的动机或者意愿上,所谓“故意侵权”是指被控侵权人“希望”产生侵权的后果或者“相信”他们的行为会确定地导致侵权结果的发生。
三、故意认定的核心:律师意见的适格性和完整性
律师意见的适格性和完整性,是认定被控侵权人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的关键。在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案[25]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采取全席判决的方式,给出了在律师意见的适格性和完整性判断中应当主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律师意见的来源,律师意见是由被控侵权人内部律师作出的意见,还是由独立的外部律师作出的意见;(2)律师意见的形式,律师意见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3)律师意见的主体,律师意见是由通行律师作出的意见,还是由专业律师作出的意见;(4)律师意见的材料,律师意见是否是在考虑了专利权有效性和侵权有关的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其中有关材料包含专利审批历史的材料;(5)律师意见的专业性,律师意见是否存在法律理解错误,或者是否存在未能充分理解和把握专利权效力和专利侵权相关理论的情况;(5)律师意见的资格,律师意见由执业专利律师作出,还是由专利代理人作出;(6)律师意见的内容,律师意见是否明确清楚。
律师意见不适格、不完整都是影响故意侵权抗辩的典型情形。其中,律师意见不适格主要通过律师意见的来源、律师意见的形式、律师意见的主体、律师意见的专业性、律师意见的资格等来判断,律师意见不完整主要通过律师意见的材料、律师意见的内容来判定。通常而言,律师意见不完整的典型表现是,律师在未看到全部必要事实的情况下作出法律意见,或者是律师在作出法律意见时没有作出必要的分析。首先,律师在未看到全部必要事实的情况下作出法律意见。
在卡马尔克通信公司诉哈瑞斯公司一案[26]中,尽管被控侵权人获得了不构成侵权的律师意见,但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基于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故意向律师隐瞒重要信息,认定被控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其次,律师在作出法律意见时没有作出必要的分析。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诉赛尔普罗公司一案[27]中,尽管被控侵权人获得的律师意见是专利权无效和不构成专利侵权行为,但是由于该律师意见忽略了其他权利要求,并且没有将引用的现有技术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联系起来,同时考虑到该公司主管精通专利法和相关技术领域,因此认定被控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
再如,在金布朗特公司诉罗伯特·H·皮特森公司一案[28]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被控侵权人构成故意侵权,主要理由是在没有分析专利申请过程和分析被控侵权产品结构的情况下,作出的不构成侵权的律师意见不具有适格性和完整性。同时,考虑到被控侵权人没有及时回应专利权人的警告函,对该专利权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因此认定被控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
四、故意认定的抗辩:被控侵权人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
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的“故意”,最为重要的抗辩理由是,被控侵权人具有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如果被控侵权人在行为过程中表现出具有避免侵犯专利权的主观动机,那么被控侵权人不具有主观故意,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例如,在博朗公司诉美国动力学合作公司一案[29]中,原告博朗公司诉称,被控侵权人没有直接回应其律师有关需要查看产品外部配置情况的请求,仅向律师发送了最终设计和试生产阶段原型的照片和设计图纸,因此被控侵权人获得的不构成侵权的律师意见不适格。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具有充足的、无可质疑的证据表明,被控侵权人采取适当的注意和明确的善意以避免专利侵权,这主要体现在,在知道该专利之前,被控侵权人聘请设计公司独立设计了搅拌机;被控侵权人的律师全程参与这一设计过程并提供了法律咨询意见;被控侵权人的律师在被控侵权人的请求下发现了该专利;被控侵权人基于“与该专利比较类似”的理由拒绝了设计出来的一种方案;当年3月17日,被控侵权人接到律师发出的信件,该信件明确表明其最终设计并不侵犯该专利权;7月29日,被控侵权人接到律师发出的信件,该信件在详细分析之后得出了不构成侵权的结论。
据此,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被控侵权人不构成故意侵权。被控侵权人实质上质疑专利侵权是否成立和专利权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导致被控侵权人缺乏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并不必然导致被控侵权人构成侵权故意。
五、故意的证明:从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到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再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回归
早期法律实践: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美国早期的法律实践中,对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在西摩诉麦考密克一案[30]中,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对于因为善意或者疏忽造成的一般侵权行为,应当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损害赔偿标准,对于因为蓄意或者恶意造成的特殊侵权行为,可以判处加倍的赔偿,不仅起到补偿专利权人损失的作用,也起到惩罚被控侵权人的作用。该案确立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前提,但是没有对“故意”的证明作出讨论。
在水下装备公司诉莫里森·努森一案[31]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民事主体在收到专利权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的时候,具有积极注意义务以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在收到专利权人发出的警告函或者律师函之后,该被控侵权人具有积极义务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被控侵权人的内部法律顾问进行了现有技术检索,但是并没有获得或者分析专利侵权行为发生之前该专利的审查历史,其法律意见在专利权的有效性和侵权判定方面仅有没有支持的结论性表述。同时,被控侵权人明知这一法律意见来自其内部法律顾问并且其内部法律顾问没有专利代理资格,因此,该内部法律意见并非适格的法律意见,被控侵权人构成故意侵权。在这一证明过程中,完全采用了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希捷公司上诉案:从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转向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在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上诉(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一案[32]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明确了“故意侵权”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其中的“客观标准”就是被控侵权人对侵犯有效的专利权的较高可能性有所认识,不顾客观上具有较高可能性构成侵权的情况,仍然轻率地、鲁莽地进行了制造、使用、销售、进口、许诺销售等行为。其中所述的“轻率地、鲁莽地”,通常是指民事主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一个理性的民事主体应当认识到,其行为是不合理的冒险行为,却仍然坚持进行这一行为[33]。为了证明这一客观标准的成立,专利权人必须以清晰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客观标准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
光环电子案和斯特赖克公司案: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回归。对“希捷标准”的反思与向完全主观标准的转变。2016年6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光环电子公司诉脉冲电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案[34]和斯特赖克公司等诉齐默公司[35]专利侵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调整了“希捷标准”[36]。
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希捷公司上诉案给出的证明标准也进行了讨论,否定了希捷公司上诉案确定的“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实现了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回归。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一方面,现行法没有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美国法律实践针对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提出的专利权无效抗辩、以在先发明人为根据的侵权抗辩等,采用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然而这些是以《美国专利法》第282条、第273条的规定作为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些条文对证明标准作出了专门的特别规定。
《美国专利法》第284条并未对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作出单独的证明标准要求,立法者并未给予特定的证明标准要求,因此,不应当适用更高的清晰可信的证明标准。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法律实践也没有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傲客健身器材公司诉爱康运动与健康公司一案[37]中所作出的考察,专利侵权诉讼一直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不应当是例外。
结语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需要实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双重价值取向,体现政策价值和经济价值[38]。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构成要件的认定中,也需要注重这二者的平衡。
通常而言,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其主要通过寻求遵循称职律师意见的情况加以认定。这一认定的关键是被控侵权人的动机或者意愿,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加以证明。关于构成要件的最关键的抗辩理由,是被控侵权人具有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也需要通过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的行为加以判定。
[1]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cazjgg/201512/2015120047959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日);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http://www.chinalaw.gov.en/article/cazjgg/20 1 406/20 1 40600396 1 8 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2日)。
[2]张鹏:《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及基本建构》,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4期,第102-107页。
[3]袁秀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司法适用》,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7期,第21-28页。
[4]参见Roberts v. Sears, Roebuck & Co.,723 F.2d 1324,221 USPQ 504(7th Cir. 1983), on remond, 1986 WL 6909(N.D.111. 1986]; Yoder Bros., Inc. v.California-Florida Plant Corp.,537 F.2d 1347,1383-84,193 USPQ 264(5th Cir.1976),cert denied,429 U.S. 1094(1977)另参见和育东著:《美国专利侵权救济》,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5]InreSeagate Technology LLC,497 F.3d 1360,2007 U.S.App.LEXIS 19768(Fed. Cir. 2007(en banc),cert. denied sub nom.
[6]Marketa Trimble Landova. Punitive damages i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actions under the US Copyright Act. E.I.P.R. 2009,31(2),p. 110.
[7]张玲:《论专利侵权赔偿损失的归责原则》,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第119-130页。
[8]Jon E. Wright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Enhanced Damages: Evolution and Analysis. 10 Geo. Mason. Law Review 97(2001-2002).
[9]Underwater Devices,Inc. v. Morrison-Knudsen Co.,Inc.,717 F.2d 1380,1390,219 USPQ 569(Fed. Cir. 1983), overruled.
[10]Kalmanv.Berlyn Corp.,914 F.2d 1473,1484,16 USPQ2d 1093,1101 (Fed. Cir. 1990).
[11]Central Soya Co.. Inc.v.Geo. A. Hormel&Co.,723 F.2d 1573,220USPQ 490(Fed. Cir. 1983).
[12]American Original Corp. v. Jenkins Food Corp., 774 F.2d 459,227 USPQ 299(Fed. Cir. 1985).
[13]King Instrument Corp. v. Otari Corp., 767 F.2d 853,226 USPQ 402(Fed. Cir. 1985),cert. denied,475 U.S. 1016(1986).
[14]Underwater Devices,Inc. v. Morrison-Knudsen Co.,Inc.,717 F.2d 1380,1390,219 USPQ 569(Fed. Cir. 1983), overruled.
[15]Kalman v. Berlyn Corp.,914 F.2d 1473,1484,16 USPQ2d 1093,1101(Fed. Cir. 1990).
[16]Read Corp.v.Portec, Inc.,970F. 2d 816, 23 U.S.P.Q.2d 1426(Fed. Cir. 1992).
[17]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497 F.3d 1360,2007 U.S.App.LEXIS 19768(Fed. Cir. 2007(en banc),cert. denied sub nom.
[18]Knorr-Bremse Systeme Fuer Nutzfahrzeuge GmbH v Dana Corp., 383 F.3d 1337(Fed. Cir. 2004).
[19]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497 F.3d 1360,2007 U.S.App.LEXIS 19768(Fed. Cir. 2007(en banc),cert. denied sub nom.
[20]Safeco Ins. Co. ofAmerica v. Burr,551 U.S. 47(2007).
[21]Randy R. Micheletti. Willful Infringement After In re Seagate: Just What Is “Objectively Reckless” Infringement? 84 Chi.-Kent L. Rev975.994-996(2010).
[22]Randy R. Micheletti. Willful Infringement After In re Seagate: Just What Is “Objectively Reckless” Infringement? 84 Chi.-Kent L. Rev.975,994-996(2010).
[23]Halo Electronics, Inc.v.Pulse Electronics, Inc., 136 S. Ct. 1923(2016),195 L.Ed.2d 278,84 USLW 4386,118 U.S.P.Q.2d 1761.
[24]Stryker Corporation, Et Al., Petitioners v. Zimmer, lnc.,Et.Al., 14-1520.
[25]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497 E3d 1360,2007 U.S.App.LEXIS 19768(Fed. Cir. 2007(en banc),cert. denied sub nom.
[26]Comark Communications,Inc.v.Harris Corp., 156 E3d 1182,48 USPQ2d 1001(Fed. Cir. 1998).
[27]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v. CellPro,lnc., 152 F.3d 1342,47 USPQ2d 1705(Fed. Cir. 1998).
[28]Golden Blount, Inc.v.Robert H. Peterson Co., 438 F.3d 1354(Fed. Cir. 2006)
[29]Braun Inc. v. Dynamic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975 F.2d 815,24 USPQ2d I121(Fed. Cir. 1992).
[30]Seymour v. McCormick-57 U.S. 480 (1853).
[31]Underwater Devices,Inc.v.Morrison-Knudsen Co.,Inc.,717 F.2d 1380,1390,219 USPQ 569(Fed. Cir. 1983), overruled.
[32]In re Seagate Technology LLC,497 F.3d 1360,2007 U.S.App.LEXIS 19768(Fed. Cir. 2007(en banc),cert. denied sub nom.
[33]Safeco Ins. Co. of America v. Burr,551 U.S. 47(2007).
[34]Halo Electronics, Inc. v. Pulse Electronics, Inc., 136 S. Ct. 1923(2016),195 L.Ed.2d 278,84 USLW 4386,118 U.S.P.Q.2d 1761
[35]Stryker Corporation, Et Al., Petitioners v.Zimmer, Inc.,Et.Al.,14-1520.
[36]张晓霞:《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的新发展》,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9期,第104-109页。
[37]Octane Fitness,LLC. v. Icon Health&Fitness,Inc.,134 S.Ct. 1749,188 L.Ed.2d 816,82 USLW 4330,110 USPQ2d 1337.
[38]张鹏:《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价值初探》,载《科技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322-3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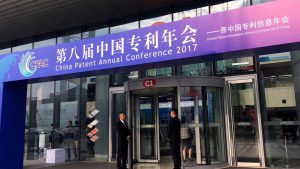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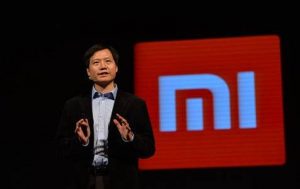





最新评论